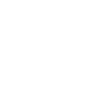这样夸耀过自己的涵养之后,我得承认,这种宽容是有限度的。为人处世的基础可以建立在坚硬的岩石上,也可以建立在潮湿的沼泽地上,但过了某一个点后,我就不管它的基础是什么了。
去年秋天从东部回来的时候,我感觉到我想要全世界穿上制服,且在道德上永远规规矩矩地立正;我不想再参加纵情狂欢的远足,从而又有机会窥视他人的内心。不在我这种反应之列的只有盖茨比,以其姓氏给本书冠名的那个人---盖茨比,他代表了我由衷鄙夷的一切。
如果说一个人的存在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成功姿态,那么可以说他身上有些耀眼夺目的东西:对于人生前景的一种高度的敏感,就仿佛他连在一台记录万里之遥的地震的复杂仪器上。这种感应力同那种软绵绵的感受能力毫不相干,后者在“创造性气质”之名下得显尊贵,而它却是一种感受希望的非凡天赋,一种富于浪漫色彩的随时做出感应的状态。我从未在其他人身上发现过这种感应力,将来大概也不会再发现。
不---最后盖茨比表明了自己没问题。是那种啃噬盖茨比的东西,是他的幻梦之船的航迹上漂浮的污浊尘埃,是我一时间兴味索然,不再关注人们的短命的伤悲和上气不接下气的得意。
在这个中西部城市,我们家作为名门富户已经有三代。卡拉伟一族也可算是个世家吧,根据代代相传的说法,我们是巴克卢公爵的后裔。其实,我这一支的创始人是我祖父的哥哥。他五十一岁时来到这里,派个替身去参加内战。自己做起了五金批发生意,由我父亲承继经营至今。
我从未见过这位伯祖父,但他们认为我长得和他很相像,有挂在父亲办公室的那幅硬派风格的画像作为特别参照。我一九一五年毕业于纽黑文,恰好比父亲晚了四分之一个世纪。没过多久,我便参加了那一场人称世界大战的延迟了的条顿民族不迁徙。反攻的时候我快活过了头,回国后便安静不下来了。我觉得中西部不再是温暖的世界中心,反而像是破烂的宇宙边缘,于是决定去东部,学做债券生意。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在做债券生意,所以我估摸着,这行当再多养活一个人没有问题。我的叔舅姑姨们全体参与,将此事谈论一番,仿佛是在为我选一所预备学校。最后他们说:“嗨,好吧。”一脸十分庄重和犹豫的神情。父亲同意资助我一年,然后几经耽搁,我终于在二十二岁那年来到东部,心想,这是奔流到海不复回了。
比较实际的办法是在城里找个房子,但当时是暖春时节,而我刚离开草坪宽阔、绿树成荫的乡间,所以,当营业所里一位年轻人提议到交通方便的镇子里合租一所房子时,我觉得这主意听起来很棒。我找到了房子,一幢饱经风霜的木板平房,月租八十美金。但在最后一分钟,公司将他调往了华盛顿,我只得独自住到郊外。我养了一条狗,至少在跑掉之前他陪了我好几天。我买了一辆道奇牌旧车,还雇了个芬兰女人,她为我整理床铺做早饭,一边在电炉上操作,一边嘀咕芬兰的至理名言。
我只孤单了一两天,然后在一天早晨,一个比我更晚来到的人在路上叫住了我。
“去西卵村怎么走?”他无助地问。
我给他指了路。接下来的一路上,我不再感到孤单。我成了向导、探路者,成了一个原住民。不经意间,他已经授予我在附近一带的自由话语权。
阳光明媚,树木忽地一下长满了树叶,就好像电影里植物生长的快镜头一样。于是那种熟悉的信念又在我心里面萌生了;随着夏天的来临,生命正重新开始。
有那么多书要读,这是其一;同时,从给予生命以呼吸的新鲜空气里,又有那么多让人健壮的养分可以汲取。我买了一打银行、信托和投资证券方面的书,红皮烫金的书一本本立在书架上,就像造币厂新出的钞票,给我应许,要向我展示那些熠熠闪光的、只有米达斯、摩根和米塞纳斯才真的的秘密。此外,我有个雄心大志,要博览群书。读大学时我颇喜欢舞文弄墨,有一年,我曾为《耶鲁新闻》写过一系列一本正经又浅显乏味的社论。现在我要将诸如此类的东西全部收回到我的人生中来,重新成为“通才”,就是那种样样通晓但都所知有限的人。这不仅仅是一句俏皮的警言---毕竟,从单独一扇窗去看人生,人生要成功的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