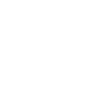文 /马付才

那时我也就十八岁吧,或者是十九岁,我不知道我该说我的虚岁,或者是周岁,反正,那时的我十八九岁,十八九岁属于我的那个秋天,是一个充满了忧伤的秋天,因为,那个秋天,我高考落榜了。
学校开学已将近两个月了,我那些考上大学的同学们早已像小鸟一样快乐地飞走了,我那些没考上大学的同学们,都又收拾好课本,坐在了高三的复读班里。
那时的我每天早上起来,用冷水从头到脚浇一遍,然后,胡乱找点吃的东西塞饱肚皮,就走到大街上开始了一天的游荡。
小镇也就是六七千人口,我常常从街东头走到街西头,又从街南头走到街北头,我一间门店一间门店就这样毫无目的浏览。小镇上许多的人都认识了我,我却不认识他们。那天我走在一个服装店的门口时就遇到了小艳,那时候并不知道她叫小艳,小艳正在与服装店的老板争吵。服装店的老板四十多岁,长的又黑又胖,他气恨恨地把手背在身后,反复地说:怎么可能呢?怎么可能呢?
小艳的手里拿着一件粉红色的上衣,小艳什么话也不说,只是把那件上衣举到老板的面前,冲他一个劲的冷笑。小艳冷笑着与老板僵持了一会儿,她说:你换不换?许多看热闹的围成了一个半圆的圈子,路边路过的人又不断加入这个圈子。人们都小声议论纷纷,于是我知道了,小艳前一天在这个服装店里买了这件粉红色的上衣,谁知这件粉红色的上衣一只袖子却是破的,粗心的小艳拿回来找店主换,店主却不承认,于是就吵了起来。
那个又矮又胖心虚的店主就硬撑在那儿,但周围却没有人替小艳说句公平话。这时,也不知什么原因,使我走上前去冲店主说:“人家在你这儿买了破衣服,你不给人家换,你说你这样做生意,以后谁还敢上你这儿买东西?”听我这么一说,于是就有人小声去劝那店主:“你不知道她是谁?得罪了这类人,以后你的生意就做不成了。”
最后是店主的退让。当小艳拿着换回的衣服时,她拍了拍我的肩膀,友好而意味深长,拍了我肩膀的小艳让我激动了好长时间。小艳走后我听周围人都议论纷纷:“哼,流氓!”也有人嘀咕说,看上去眉清目秀的我,怎么会和女流氓是一伙的。
这些议论我都听到了,天啊,她怎么会是流氓?她看上去最多也就十五六岁,她的眉毛又弯又细是天生的,她的眼睛又大又圆是明亮的,她的嘴唇又鲜又红是自然的,这一切一切,都与流氓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,显然,人们把我当成了和她是一伙的。
第二天,在街上闲走时,小艳又出现了,显然,是她在街头等我的,她大声和我打着招呼,我看见她那漂亮得出奇的脸上的笑,绝对是一种纯真率朗的笑,那笑让任何富有想象力的人也想不到,有这样笑的女孩会是一个女流氓。
于是我们相识了。她告诉我,她叫小艳。
小艳有一辆红色的坤车,她让我坐在她的坤车后面,她骑着坤车飞快地在街道上穿行,撒下的一路铃声,让路上的行人纷纷躲闪。躲闪的行人纷纷向我们吐口水,咒骂我们,不过,我们看不到也听不见,因为我们的欢声笑语覆盖了大街上噪杂的喧闹声。
小镇外就是秋天的田野。大豆已经结荚了,玉米已经挂棒了,棉花的蕾铃快要盛开了。我和小艳气喘吁吁地来到一片玉米地的田埂边,坐在青青的草地上,仰望着蓝蓝的秋空,以少年的纯真和向往,谈论着少年时的快乐和烦恼,红颜知己一般。那一天,我们都忘记了烦恼,那一天,是我高考落榜后过得最开心的一天。

晚上回到家中,父亲面对我照例是在叹气,他说:“小帆,你这样游荡也不是个办法,你想过你以后该怎么办吗?”父亲的话让我轻松一天的心又沉重起来,是啊,我该怎么办?
我的父亲在小镇上开了一家烟酒小店,小店里出售着劣质的香烟和散装的白酒。小店里凌乱不堪,处处落满了灰尘,我一回到这烟酒小店里,心里也落满了灰尘,一点也快乐不起来。难道我就这样无所事事,然后继承父亲的烟酒小店,做一个灰头灰脸的小老板?其实这个问题父亲和母亲已讨论了无数次了。但像我父亲这样身份卑微的人,他只会毫无能力地叹气。那天晚上父亲想了许久才对我说:“要不,你去当兵去吧,你是高中毕业,当兵说不定还能考上军校,即使考不上军校,也能在军校学点技术,或者转业也好找个工作。”
父亲说的这也是一条出路,在我们那个小镇上,当兵也是走出去的一个门路,只不过,当兵也不是容易的,许多人都想挤着当兵,像我这样没有头脸没有门路的人,能当兵走的希望太渺茫了。父亲对母亲说:“要不,去找找海永吧。”海永是我的舅舅,我的舅舅在县城一家单位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,他就是一个复转军人,或许会有一些门路。母亲想了想,也只好这样了。
第二天,一大早母亲就叫醒了我,草草吃了点饭,母亲让我把鸡笼里两只下蛋的老母鸡抓了出来,用绳子拴好,装进了一个蛇皮袋里,母亲让我跟她一起去县城舅舅家去,临出门走时,母亲想了想,又让我把家中那只常常下双黄蛋的老黑鸭也装进了蛇皮袋里。小镇距离县城四十多里地,我骑着我家那辆二八加重自行车,后边坐着母亲,母亲把蛇皮袋抱在怀中,一路上,那两只老母鸡和一只老黑鸭都温顺地呆着,不叫也不挣扎,它们根本不知道,一进县城我舅舅家,它们的生命就戛然而止了。
舅舅家住在县城里的一幢民房里,舅母一看是我和母亲来了,脸上就显出了不高兴,直到母亲把蛇皮袋里面的两只母鸡和一只老黑鸭拎了出来,问她放在哪里,她脸上才露出了点笑容。
舅母中午在厨房做饭时,母亲才在客厅里面把我想当兵的事告诉了她的弟弟,想不到舅舅答应得很爽快,他说:没关系,从镇上的武装部到部队里他都认识一些人。我当兵的事好像就这样定了下来,回家时,我和母亲都是一路欢喜,母亲说:课本不能丢,我说,嗯。母亲说:要考军校。我说:考军校。

回到小镇上我又见到了小艳。见到小艳时,她的眼窝青青的,半边脸也是青青的。我问小艳你这是怎么了,小艳说是被人打的,我握紧了拳头说:是哪个狗日的?小艳说:是我爸。我握紧的拳头就又松开了。我说:小艳,对不起,我不知道是你爸。
小艳说,他就是狗日的,狗日的要卖我哩,我才十六岁,我不能让狗日的把我卖给收废品的刘老二。
刘老二我知道,在街头开了个废品收购部,整天摆弄那些脏兮兮的废铜烂铁,刘老二因此也脏兮兮的,头发老长,一缕一缕,胡子老长,乱七八糟,指甲老长,藏污纳垢让人看着都恶心。不过,狗日的刘老二可发了财,谁也不知道他存折上存了多少钱,整天与废品打交道的刘老二都三十岁了,小艳他爸真是财迷心窍了,让狗日的刘老二老牛吃嫩草。
小艳一脸的忧伤,不过,很快她又快乐起来了。她说:好了,不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了,我方小艳可不是那种贱女人,也不是那种好欺负的女人。天啊,小艳说她是女人。我当时误解了小艳,现在,城市里的女人都三十多岁了,还处处称自己是女孩哩,她们还真是女孩吗?其实,小艳在我眼中才是一个小不点儿的女孩子,她就像我家院中去年刚栽种上的那棵小杨树,那是一棵正在成长的树啊。
小艳扔给我一支香烟,她自己也点上一支,我吸了两口,呛得眼泪都流了出来,她连忙把烟从我嘴上拿下来,用脚把它踩灭,她说:对了,你不会抽烟,你是个高中毕业生,哪能跟我们一样呢?不会抽烟你就别学这玩意了。
小艳说的“我们”我知道是她的那些朋友们。小艳的那些朋友们。我知道有街东头的小刚,小刚他爸是杀猪的王大海,小刚他妈早病死了。王大海一脸横肉,嘴里噙着一把杀猪刀,他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,小刚像他爸王大海一样,初中没毕业就跟着他爸杀猪了,也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,谁敢惹小刚?小艳的朋友我知道还有大强,大强他爸是我们镇政府食堂里的厨子周思见,周思见长得又白又胖,整天眯着一只眼,见人就笑。他的儿子周大强却是又黑又瘦,根本就不像他种下的种。周思见好像也看出来了,周思见就打他的老婆,他老婆就杀猪般地嚎叫着,骂他是“龟儿子”,周思见他老婆是四川人,她的叫骂半条街的人都能听到。周思见又用目光寻找周大强,周大强蜷缩在一旁目光里满是畏惧。周思见轻蔑地看一眼他这个儿子,恨恨地骂:野种!野种!
周大强十二岁起就开始在镇上弄些袜子、裤头之类的东西,放在塑料单上摆起了地摊,周大强的地摊挨着王小刚的肉摊,王大海杀猪王小刚卖肉,逢集人多时,两个稚嫩的声音此起彼伏:卖肉呀——谁要袜子裤头——还有一个声音是方小艳的,小艳弄了个眼睛摊,架子上挂满了太阳镜,遮光镜什么的,小艳也戴着一个太阳镜,有时候是蓝镜片,有时候是黑镜片,还有时候是黄镜片。小艳戴着太阳镜就是一个活广告,她挽着头发,抹着口红,双手叉着腰,一点也不像十六岁的样子。小刚、大强和小艳的摊位一个挨着一个,有时候谁有点事离开一会儿,另两个就会自觉地帮他看着,如果这一天谁的生意特别好,就会请上另外两个或者是去小镇东边的影剧院看电影,或者是去小饭馆撮一顿,他们一起抽烟,一起喝酒,一起骂娘,小镇上许多人们都冷眼看着他们,对此我并不感到奇怪,那些心怀善良而又热爱光明的人们,他们一定把小艳和她的朋友们当成了教育儿女成材的反面教材,而且,他们大多也会顺便提及到我,因为,我也成了小艳还有她朋友们的朋友,他们会说我,一个曾经很好的孩子,怎样跟着小艳变成了一只令人讨厌的苍蝇。
我无所事事,我挣不来钱,连自己也养活不来,小刚大强小艳他们吃饭看电影大都要喊上我,我却推推脱脱有点不好意思,小艳用手随随便便拍拍我的肩膀,她说:走吧,别不好意思。我说:你们每次都叫上我,我还没请过你们呢?小艳说:那有什么?我们是哥们了,你还这么小家子气?
小艳总是这个样子,她泼悍,倔强不训,一点也不像个女孩子的样子。那时候我看过《红楼梦》,看过《红与黑》,还喜欢看“啊,梦中的女孩”之类抒情的诗歌,整天把自己弄得多愁善感的,想,像小艳这样的女孩子,应该是羞羞答答的,那样才像淑女的样子。那时候,我还想小艳会不会真的是一个女流氓呢?我仔细观察过小艳和小刚,小艳和大强的关系,结果我发现,十八九岁的我真是太肮脏,太复杂也太卑鄙了。小艳和她的朋友们可以吸烟,可以喝酒,可以看电影,但他们绝对是很阳光的友谊,他们的交往不存在有杂念,他们在别人的冷嘲热讽和鄙视中,真诚帮助,互相团结,他们只是倒弄些东西挣些小钱,偷盗,抢劫之类的事他们从来没干过。现在,我知道小艳和她的朋友们大都做小买卖到大买卖而发了财,当许多人认为他们的钱都来路不正而咬牙切齿时,只有我知道他们在社会底层曾经是怎样艰辛地挣扎。
父亲很快知道了我和小艳他们搅合在一起。父亲恨铁不成钢地对我说:你看你混成什么样子了?你看你堕落到哪里了?我的嘴也挺倔强,说:我怎么啦?父亲说:怎么啦?你跟流氓鬼混在一起,还说怎么啦?我说:你说话得有根据,谁是流氓啦。
父亲气得咬牙切齿,他说:方大头这个赌棍能养出什么好闺女,你们那些事我知道得一清二楚。我反而不生气了,我笑了,我说:亲爱的爸爸,看人不能只看表面现象,如果你真知道得一清二楚,你就会知道,你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。
我把我父亲气得说不出话来,他手指着我,你你你了好长时间,却什么也没“你出来”。我想,我父亲是糊涂了,小镇上的人都糊涂了。

父亲从此就不再让我出去游荡,他把我高中时的书本都找出来了,他说:你好好复习功课吧,准备着当兵,准备着上军校。父亲说的是那样的肯定,好像我一定能当上兵,当上兵就一定能考上军校似的,我知道父亲想是肯定的,我舅舅都答应了,我舅舅是谁?他是县城一个单位里一个不大不小的官,镇上武装部有他的朋友,部队里来的接兵的有他的战友,或者是他战友的战友,舅舅都答应的事肯定能成。
我已经有三天没见到小艳了,没见到小艳每天我的日子都过得度日如年。那时候我们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话,我想,小艳会在干什么呢?第四天的时候小刚和大强来找我了,小刚和大强来找我不敢直接来我家敲我们的门,他们在我家的房后面用砖头不轻不重地敲了几下,然后,吹了两声很响亮的口哨声。这是我们商量好的暗号,我父亲把我囚禁在屋中让我学习ABC和XYZ,他说我不能跟着一个杀猪的酒鬼的儿子学坏了,也不能跟着一个没人管的杂种乱跑,小刚和大强知道了这些就不敢光明正大地上我家约我了。
我呆在屋中一点也学不进去ABC和XYZ,如果我能学进去,凭我聪明早在高中时就考上大学了,听到小刚和大强的口哨声我的心立刻就飞了出去。不过,我得装着什么事也没有,一点也不能急躁一点也不能兴奋,我稍稍停了一会儿才走到父亲身边,我说:爸,有一道数学题我不会做,我想去请教请教李老师。李老师在镇中教学,是我家的邻居。父亲一听我说的是学问上的事,就立刻摆了摆手绿灯放行。我兴奋得心都要跳出来了,一走出父亲的视线,立刻像笼中的小鸟飞回了大自然。
小刚和大强等得已有点焦急,我一看就他两个,不见小艳的影子,就问:小艳呢?
小刚和大强就告诉我说:找你就是为了小艳,小艳被狗日的方大头锁在屋中了,狗日的方大头赌博欠了人家五万元钱,他要把小艳卖给收废品的刘老二,狗日的刘老二都三十了,你说我们能答应吗?我立刻很干脆很坚决地说:不答应。我们把小艳当成了我们的妹妹,其实我十八九岁,小艳十六岁,小刚和大强一个十五岁一个才十四岁。
小刚和大强想到小艳家把小艳救出来,他们想到了我,叫上我做他们的帮手,我们都是哥们,为哥们两肋插刀那是应该的。我们一行三个人浩浩荡荡地来到小艳家,站在门外一齐喊:小艳——小艳——
小艳在里面听到了,她趴在窗户上,把手从窗户空里伸出来,兴奋地向我们招手,小艳都快要绝望了,现在,她看到我们,她不绝望了。
方大头出来恶狠狠地说:嚎!穷嚎个什么?这是一张典型的赌徒的眼睛,眼圈发黑,眼睛布满了红血丝。我们说:你把小艳放出来!
方大头说:放不放关你们屁事。我说:方大头,小艳是不是你女儿,是你女儿你就不应该这样对待她,她才十六岁,你赌博已经犯法了,现在你还想再犯法,信不信我去告你去?小艳在屋中大声说:你不是我爸,你赌博已经逼死了我妈,现在还想逼死我,我死给你看你高兴了吧。周围许多人都围了上来看热闹,方大头立刻软了,他看看周围一张张面孔,一张张面孔充满了鄙夷。他把头勾了下去,过去把锁打开,再也不敢看任何人。那一时刻我才觉得,其实这个方大头是多么的渺小,小艳走了出来,她头发凌乱,脸色苍白,眼睛深陷,解放出来了的小艳,没有一丝高兴的样子,她走到方大头的面前,跪了下来,说:以后只要你不赌了,你还是我爸,你老了我还要养活你。
那天我一回家父亲就给了我一个耳光,我们今天做的事父亲又全都知道了,血顺着我的嘴角就流了下来,它流到我的衣服上,又流到我的脚背上,我冷冷地看着我的父亲,我想说:父亲,我没有错,你为什么打我。我不会给父亲说的,说了父亲也不懂。我想,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的心都像父亲一样,这个世界就完了。
从那天起父亲把我看得更紧了,他不让我出去,让我呆在屋中,面前就放着语文、数学、英语的课本,然而,我的眼睛盯着那些书本里面的文字,心却根本进不到里面去。我就这样坐着,脑子里整天想着许多乱七八糟的事和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。

冬天终于来了,征兵终于开始了。我知道,自从我和母亲去了舅舅家回来后,我们一家就一直为我能去当兵而准备了。现在,征兵终于开始了,母亲领着我决定再去一趟舅舅家。去的时候,我们带了半蛇皮袋红薯和半蛇皮袋绿豆。舅舅突然对我当兵的事不热情起来,他说:当兵有什么好,当兵吃苦受累又不挣钱,不如让小帆做个小生意,再说了,当兵也不一定让考军校,让考军校你也不一定就能考上军校。舅舅的突然变化让我和母亲都摸不着头脑,舅舅对我当兵的事变冷淡了,他不热情了,如果他不热情,那我就有可能当不成兵,你不知道,在我们那个小镇上,有许多有钱有势有头脸的人,都想把他们的儿子送到部队上去锻炼锻炼,然后再找个出路。我能挤过李冰志吧?不能。他父亲可是我们镇的副镇长,我能挤过曹雪山吧?不能。他父亲可是我们镇派出所的指导员,我能挤过丁光盛吧?不能。他父亲可是我们镇计生办的主任。还有,还有许多我不知道的人,他们都想在那一年当兵,你说,如果我舅舅不管我了,我还能当成兵不?
那一年征兵报名时,我遇到了董浩,董浩是我舅妈的娘家侄儿,一遇见董浩我的心不由一惊,不过,我立刻又放松了,因为我知道董浩,董浩是个罗圈腿,董浩还是个色盲眼,就凭这两点,董浩是不符合当兵条件的。我太天真了,那时我怎么也不想想,明知不符合条件的董浩来报名当兵,那肯定是有人照顾的。
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,雪早早就飘落了。我陪着别人一起报了名,陪着别人一起体过检,然后,我就傻乎乎地回来了,直等到新兵发下服装,直等到新兵坐上火车,我才彻底明白,我只是别人的陪衬,当兵的路彻底堵死了。
后来时间长了,我们一家都知道了,董浩当上了兵,光荣地成了某空军后勤部队的一名战士。这时,我们一家才明白,我们是被人欺骗了,被人愚弄了,那鸡鸭白送了,那红薯绿豆我舅舅一家能吃上好长时间吧。父亲也管我不太严了,我又可以偷偷地跑出去玩了,小艳还在卖眼镜,只不过不卖太阳镜了,冬天的生意很是清淡。小艳也少了许多爽朗的笑,那曾经的笑让街上许多人侧目相看,又让许多人纷纷吐痰。我想,小艳这是怎么啦?她才十六岁,十六岁正是少女的花季,十六岁正是一棵成长的小树,她不应该和我一样有忧伤。小艳不笑的时候很象一个淑女,不过,我又不愿意看到小艳像个淑女的样子。
我也是蔫不拉唧,小艳说:我知道你没当上兵。我的脸微微发红,你不知道,我早就对小艳说我要当兵了,我舅舅都答应了,他那么肯定,我没有理由当不成兵,小艳和我就常常提起当兵的事,我说,我当上兵第一封信就写给你,我当上兵照一张穿军装,挎着冲锋枪的照片给你,小艳的一双眼睛就熠熠生辉,说:真的,我说:真的。那时我说的就跟真的一样,现在,新兵们早已被列车运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,然而,当兵走的却不是我,走的是那个罗圈腿色盲眼的董浩,我被我舅舅欺骗了,如果欺骗我的人和我没有一点关系,也许我还不会生气,但是,他是我舅舅,我母亲的亲弟弟,他还不如小艳,不如小刚,不如大强,不如我的许许多多的朋友们,他已经给我的心灵造成了伤害。

那个冬天,小镇上发了财的一个老板,在小镇上建起了小镇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舞厅,小镇上善良而淳朴的人们,对那些搂搂抱抱的行为颇为反感,他们都教育他们的子女永远不许去那个舞厅,那个老板仿佛也成了一个教唆犯一样,成了善良而淳朴人们的众矢之的。
一天晚上,我偷偷跑了出来,跟小艳一起去了那个舞厅,我一直以为小艳会跳舞的,像我们这样的“流氓”,所有的人都以为我们应该会搂搂抱抱的跳舞的,进去了之后,我才知道我不会跳舞,小艳也不会跳舞,我们只是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看别人跳舞,在缤纷的灯光下我看见小艳用手支着下巴,眼神里充满了忧郁和伤感。小艳说:你以后别跟我一起了,也别来这个地方了,你是高中生,该多读些书,读书是有好处的,跟着我你会学坏的。
我说:小艳,你是一棵正在成长的树,我们没有良好的环境,没有丰腴的土壤,我们只有依靠自己生长,许多人没有走到那倒霉的一步,只会对别人指指点点,我并不以为你怎么坏。
小艳一下子抓住了我的手,她和我离得那么近,从她身上弥漫出的青春气息无声无息地在变幻的灯光中散发,我们谁都没有动,也没有再说什么,彼此凝望着已泪痕满面。
走出舞厅的门口,我父亲一下子从一个黑暗的角落里窜了出来,他已经盯梢和守侯了我们许久。他一把抓住我的脖领,说:以后你再跟这个女流氓鬼混,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!我看见小艳的目光中射出了仇恨的光芒,但她看着在父亲手中无声挣扎着的我,瞬即又黯淡下去了。我看见小艳手捂着脸转身跑开了,那一时刻,我只是憋闷得难受,想叫小艳,却什么也说不出来,那是我和小艳在一起的日子里,唯一的一次见她这个刚强、泼辣、倔强不训的女孩流泪,如果我对人们说,我和小艳之间是清白的,谁又会相信我们呢?
第二天,我在街口等了许久,再也没有见小艳骑着那辆坤车飞也似地奔过来,第三天,没有,第四天,也没有。后来我去找了小刚,找了大强,他们告诉我,小艳已经去了南方,她在冬天的雨雾中去了南方,她走时,让他们告诉我,那棵小树会自己生长成一棵参天大树的。小刚和大强都不明白小艳这句话的意思,但他们原话转述了,我说:谢谢你,小刚,谢谢你,大强。
再后来,我也背着流浪的行囊,漂泊进了都市滚滚的人流中,生存的艰辛使我居无定所,渐渐地便失去了与小艳的联系,不过,我听说小艳在南方已拥有了自己的门店,手下有四五个和她一样有朝气的男孩和女孩叫她艳姐或老板。今天,当我拥有了更加成熟的理智和生活经历后,我更加坚信,小艳是一个好人,无论别人怎么说。只是,小艳或许不知道,我一直在等待着我们所说过的那棵成长的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