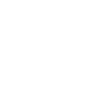前几天,叶蓓在微博上发了一段视频。在1985年众星演唱《We are the World》的录制现场,其他人都摇摆身体,动情演唱,只有鲍勃·迪伦,一副“我是谁,我在哪儿,这些人都在扭什么?”的疏离和迷糊。叶蓓评论:迪伦是少数清醒派。
看起来,叶蓓这几年在歌坛的状态,和视频里的迪伦差不多,远远徘徊于众声喧哗之外。这种已经持续了9个年头的状态在近期被打破了。

2017年9月27日,歌手叶蓓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采访。
和《环球人物》记者的采访约在一家日料店。叶蓓穿着一袭长袍,坐在对面的榻榻米上,对着镜头,眨眼笑了笑。
“好样的!”一旁的摄像记者说,这样的光线、角度最合适。
“好样的,感觉我像个英雄。”叶蓓笑了,“其实我特别不适合拍视频,我说话总是带着各种各样的零碎,废话特别多。”
一下子回到工作状态,叶蓓说自己还没习惯这样快速的节奏。这张时隔9年的新专辑,标志着她的成长和蜕变。由“白衣飘飘的年代”走过,如今的叶蓓褪去了青春的最后一点纠结与矫情,成了更为清醒、坚定的唱作人。在《流浪途中爱上你》中,她唱着“我和每一分每一秒道别离”,声音里的纯净与忧伤一如往昔。
流浪途中爱上你
专辑里的词曲,全部出自叶蓓之手,于她而言,这是第一次。“做这张唱片的时候,对它没有期许,只想尽量把自己心里的一个梦认真地描述出来,它是一种充满幻想的色彩,一种我对理想生活的描述。”叶蓓对《环球人物》记者说。
她拿着麦克风,实地收录了许多大自然的声音,风声、海浪声、火车的轰鸣、寺院的鸟鸣,用在歌曲里。“这个体验很有意思,它不是工业化的音乐,而是一个家庭作坊,你自己操刀,主导自己想要呈现的感受。”
《流浪途中爱上你》是新专辑的第一首歌,8月推出,叶蓓请来许巍一起合唱。两人上一次合作是16年前。2001年,叶蓓推出第二张专辑《双鱼》,许巍是制作人。每次录音,叶蓓都光着脚,关掉头顶的灯,只留一盏小灯夹在谱架上。“每段歌录完,透过微弱的灯光,看到老许在大玻璃外调控台前的剪影,心里就很踏实。”叶蓓说。

那时,许巍比较内向,不善言谈。“录《蓝色》时,有一两句总被他卡掉,我就有点挂脸儿了。”两个人干脆休息一天,去后海划船,爬香山,看花鸟鱼虫,“以一种柔软的方式,彼此和解”。
这次两人再合作,叶蓓很兴奋。录音那晚,她失眠了,“感慨此生的遇见,那些曾经的美好依旧如故”。“以前我们俩交流,还有些敏感、谨慎,现在是豁达、大胆和积极。”在棚里,叶蓓教给许巍一个发声方法,许巍说真好用,声音马上就不一样了。他平时唱歌,口腔不太打开,这样一打开,声音质感就变了,他自己也吓了一跳,这么好听。
现在的许巍,不再如以往一样忧郁,变得有力、温暖。这也正是叶蓓找他来合唱的原因。“几年前,我开始禅修,知道了什么是慈悲、爱和善意。冥冥之中发现,即使陷入低谷,依然会有一盏温暖的灯守护着你。”叶蓓说,“《流浪途中爱上你》是一首关于信仰的作品。我希望有男声和女声两个角色,用两个音区来传递一种能量。”

双鱼座的叶蓓,感性、纯粹而富于理想。“你最欣赏自己性格的哪一点?”这是记者来之前,在《环球人物》线上增刊征集到的一条网友提问。“善良、真实、朴素。”她不假思索地回答。这3个关键词,也正是叶蓓作品中的那份温暖所在。
几年里,叶蓓就这样一首首地写,苦心经营着自己的音乐作坊,“你要确认每一个音符和每一个字符,要让它呈现你喜欢的色彩,想好用什么样的乐器,用什么样的编曲方式……当我第一次听到完成后的作品时,简直有流泪的冲动。”
录音快完成时,叶蓓给高晓松打了个电话,告诉他整张专辑都是自己的创作。当年,高晓松让她学着写歌,叶蓓说完全不会,高晓松就告诉她:“你就写你们家,214号楼1门14号,写这个门牌号里发生的故事。”“我和他说,就因为你当年这句话,我开始陆陆续续地写歌,每张唱片都叠加一点自己的创作,终于现在整张都是我的了。”
青春无悔
叶蓓说,高晓松是改变她人生的人。
1995年,叶蓓在中国音乐学院读大一,一边读书一边在外面演出。她先在酒店大堂弹钢琴,觉得没劲,又跑去一家酒吧驻场,唱邓丽君的《千言万语》、苏芮的《心痛的感觉》、王菲的《执迷不悔》,也唱卡朋特和麦当娜的英文歌。
一天晚上,叶蓓穿着妈妈陪她在隆福寺买的丝绒质地演出服,唱起了凤飞飞的《老情人》。底下坐着高晓松、郑钧和谢东。听完叶蓓的演唱,高晓松向她要了联系方式,请她录个小样,给大明星学唱。叶蓓问,都谁是大明星啊?高晓松说了一串名字,其中就有老狼。

一个月后,叶蓓接到高晓松电话。她冒着雪,坐公交车、倒地铁,到阜成门中国银行集合。在那里她第一次见到了老狼。那时,老狼刚刚在春晚唱了《同桌的你》,粉丝无数。在银行排队的人认出了他,挤过来要签名。那晚,在小柯家里,他们录了4首歌的小样,分别是《青春无悔》《白衣飘飘的年代》《回声》《B小调雨后》。
大概又过了一年,高晓松来电话,告诉叶蓓要正式录音了。录音的工作通常在晚上8点后进行,叶蓓的妈妈不放心,跟着她去。那些年,高晓松和老狼都很瘦,长发披肩、满脸青春痘,格子衬衣皮夹克,腰上露着拴打火机的银链子,典型的不正经青年打扮。每次一见到叶蓓妈妈,高晓松就说,“阿姨,以后录音您别来了,我们都是好人。”这话一说,叶蓓妈妈更不踏实了。
录《青春无悔》的那天晚上,录音棚里黑着灯,大家都光着脚。唱的时候,老狼哭了,说他想起和女友一起在学校门口树上刻下的字。写歌的高晓松,也已收敛起了浪子的不羁,过起上班、下班、开会、领工资的日子。只有22岁的叶蓓,仍处在茫然的阶段,还没有青春已逝的沧桑。
1996年,《青春无悔》专辑一推出就火了,收到歌迷们好几麻袋的信。同年,叶蓓签约麦田音乐,和大家一起坐着绿皮火车,去各地巡演,基本都是进校园。
“在学校的礼堂唱完,就到了熄灯时间,学生们打着手电筒为我们照路,一路都有人跟着你。宿舍楼里的学生也都打开窗子,探出身叫你的名字。”对于这些画面,叶蓓至今记忆犹新,“有时会看到男生们站在女生宿舍楼下,高唱‘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’,女生们开窗,一边哭一边看着他们,特别美好、干净。”
那时候,叶蓓成天跟老狼、高晓松、朴树、宋柯这些人混在一起,吃公司阿姨做的饭,玩扑克牌,聊人生、聊艺术、聊生活、聊爱情。“我那个时候就是一个跟屁虫,他们都叫我‘后院儿的小白菜’,不能便宜了谁,随便摘走。”

2015年,老狼和叶蓓在北京保利剧院,共唱《青春无悔》。
作为“后院儿的小白菜”,叶蓓跟着这些哥哥们一起,无杂念地成长。
“狼哥比较温和,替别人着想;晓松是天蝎座,才华横溢,黑白分明。他们都是意见领袖,都有自己的思想。我在这些特别‘起范儿’的人中间,不用动脑子,他们说什么我就听什么,哪怕是看他们在饭桌上吵架,也挺有意思。”
在麦田,叶蓓和朴树就是公司的“没头脑”和“不高兴”,“因为他总是闷闷不乐,我总是没心没肺”。朴树第一次见到叶蓓,觉得她怎么能这么乐呵,在他看来,歌手不是世故得一塌糊涂,就该像他一样整天哭丧着脸。
在《青春无悔》里,叶蓓唱了一首《回声》,是高晓松献给海子的奠词:“你挥一挥手,正好太阳刺进我眼睛,我终于没能,听清你说的是不是再见。”高晓松一语成谶,这个短暂而传奇的校园民谣时代,终于在20世纪末画上句号。
此间的少年
叶蓓赶上了校园民谣最后的辉煌。后来,唱片市场慢慢变差,校园民谣也渐渐降温,圈子里的人回归到各自的生活中。
高晓松搬到了美国,拍电影、搞音乐、当评委、录节目,忙得不亦乐乎;老狼比较慵懒,结婚生娃后基本上是半退休状态,参加了《歌手》,又体会了一把“翻红”的滋味;朴树还是闷闷不乐,深居简出,今年4月,时隔14年,终于出了第三张专辑《猎户星座》,“归来仍是少年”。

有一段时间,叶蓓把自己搞得很忙,拎着箱子到处走。“我开始有了逆反情绪,‘校园民谣’这个符号,总是被拿来过度消耗,我很不耐烦,想着哪怕全世界没人听你的新歌,我也不唱老歌,但是一登台,被要求唱的依旧是那几首能想得到的作品。”叶蓓说。2008年,她决定淡出,结了婚,回归家庭,过起了最普通的生活。
2012年,高晓松在五棵松体育馆举办作品音乐会“此间的少年”。“舞台上的人都是当年的原班人马,一切那么熟悉,但又有一些抽离。”叶蓓回忆道。她身穿白裙,梳着辫子,《白衣飘飘的年代》前奏响起,所有的青春画面浮现眼前。她唱完第一句就哽咽了,眼泪顺着两颊往下掉,底下的观众也流泪了。“那一刻真的觉得青春无悔,因为我的名字与一代人最美好的青春记忆相连。”
这些年里,叶蓓认认真真地感受生活。每天练琴,做运动,买菜,观察街上最细小的场景,听寺庙里的钟声、铃铛声和小鸟叫。新专辑中有一首《红蜻蜓》,是她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一位朋友的。“红蜻蜓经过十几次蜕变才能飞出水面,它的一生是我向往的状态,无论经历多少悲欢离合,都是轻盈的,落到哪里都是家。”

“现在的你还想回到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吗?”记者问。
“不愿意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因为我已经长大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