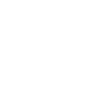友人要讲张爱玲,读书会推介读胡兰成的《今生今世》,我没有读过,只好从电脑上下载来读,委实隹作。也让我对张爱玲有了一些的新的认知:
我认为,今日的“张热”与六十多年前那个时代的“张热”是不一样的。
张走红是有其历史原因的,
日据时代的文化荒芜,大批文化学者离开了上海,还有就是日伪政府需要一种宣传和文学的“繁荣”,而熟悉上海言情生活又具有天才写作能力、带有贵族气息、知识分子气息、小市民气息的创作,自然就成为其不可多得、唯其可成的文学史痕迹
。这样的文学形象,自然与那时上海的气氛、上海人的性格相衔接,那种典型环境、人物、故事产生了1943年到1944年的“张热”现象。
张与胡的关系,由于只有《今生今世》这一本书的答案,可以说是“张爱胡说”。
胡是旧式才子追求现世利益,旧式文人的大部内涵加上时代烙痕、利益取舍。是当时之“势”造就了这一“奸狭”之士。
而张呢,却又是新式叛逆女性却有着深厚的旧式情怀,现世的天才女子,带着一种反上的“俄的普世”情结,使这两颗看似不能相碰的心在以“文学的形式”上碰撞出了火花,或者叫做“才子隹人式”的碰撞。
不同的境界,演绎出了这一出“才子隹人式”的悲剧。
胡是以自己前程命运为第一考虑的,至于“女人”,那种“如衣服”的命运,贯穿在整个封建社会全部男人的劣根性之中
,这在胡说的《今生今世》中表述得再清楚不过了。当然,他与张的感情跟其他七个女人或许不一样,这在《民国女子》的别的章节中可以看出来,那是因为张的旧式情怀,真正的至情和从一而终,追求完美的真诚的爱。
这就是张爱玲,贵族家庭、少年叛逆、聪明灵慧、细节完美,一如她的小说,唯美主义性格特征、标准化的内心世界,叫人缠绵不绝
。她也想从胡兰成的学问和才气中,得到升华,幻想有一个忠恕宽容、动人秉赋的好丈夫,可是最终失望了。
今天的“张热”,只是一种“消费”形式的
,今天的人们,从她的作品、她的出身、她与胡的恋爱、诚挚与痴情、聪慧与糊涂以及追求完美的生活习惯、孤高独处的人生经历而产生的一种认知渴望。其实想来,仔细回味,抛开43年、44年现年不说,张以后的日子,没有多少是顺心的,这也就限制了她成就更高水准的文学大师级的发展方向,这的确是一种苍凉,是张本身的“苍凉”,也是世人的“苍凉”。
这种“苍凉”,她的经历、家庭背景、少年时代的离乱、战争等,是一种因素,但与胡的感情纠葛,也是不可排除的因素吧。
假如是在和平自由的日子里,人世的温情与天佑其才,她的命运会更靠近大师的存在在,单从自己的内在感受上说,她的写作与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写法有一比,我想,如果不是生活的沦落与离散,她会写出更好的作品
。也许会有中国的《追忆逝水年华》。
但是,张爱玲没有写出这样的作品。
对于张的作品,我认为,50年代中期张爱玲已完成她最好的创作。以后的40年与其说张爱玲仍在创作,倒不如说她不断地“被”创作:被学院里的评家学者、学院外的作家读者,一再重塑金身。
她的整个创作的黄金时期,就是短短三年,正直国家烽火,多事之秋,匹夫尚且难堪,况一弱质女子。
所以,张爱玲笔下的白流苏也罢,曼桢也罢,七巧也罢…… 往往是雨打风漂萍的被动式的接受命运
。因此,她的世界,是一个荒凉的,虚无的世界。而这正是她要表达的一种态度,是对个人,对生命的一种关注,而不是历史的,负责任的
。
这就是命运,逃脱不了的命运,天才也逃脱不了
。 
我看过张的一本传记,说是五十年代初,作为上海文化界的最高负责人、副市长夏衍曾成立了上海电影剧本研究所,夏衍任所长,柯灵任副所长。这两人都是非常欣赏张的,想让她进该所担任编剧,但由于有人对张的背景持否定态度,只好暂时搁置一段,等时机成熟再通告张上班的。
1950年7月上海市第一届文代会张也参加了,穿着旗袍在列宁装、中山装之中,尽管有些不自由、压抑,
但这段日子还是以梁京的笔名写出了《十八春》和《小艾》等好作品
。1952年11月离开上海后,一直不堪生活的重负,到香港、美国都有谋生的艰难,我亦为之惋惜。
1972年以后版税多了,日子好过了,却没有写作的激情和生命的春天了。
多乖的命运限制了她的唯美主义人生追求,或者说唯美主义人生追求限制了她的文学创作。
对于爱情,我个人认为她没有多少父爱,一直在追求一种父爱的行进之中,胡比她大十四岁,赖雅比她大29岁,头一次爱情是为文学,第二次是以文学为引子,实为生活、生存。
胡兰成讲述他与她的相识,相爱,讲述她所说的“欲仙欲死”,她的“见了他,她变得很低很低,低到尘埃里,但她心里是欢喜的,从尘埃里开出花来”,
实际上是一种消费
,正如止庵所说:
迄今为止,除她本人提出异议外,我们几乎找不到其他反对或佐证的材料。说来坊间各种张爱玲传记,无一不从《今生今世》中取材;研究者只顾着翻故纸堆,却与世间若乾重要人物失之交臂;於是胡兰成得以“趁虚而入”,《今生今世》遂为“空前绝后”。
假如另有一册“炎樱回忆录”或“姑姑回忆录”以为参照,那么面对此书,也就不难乾点儿去伪存真的事了。
现在我们只好专听胡兰成的,听罢照样可以讨厌他,甚至骂他。
因为是“孤本”,那么不是一种消费是什么?
他是旧式才子,却不袭旧式文化传统:母丧不归,效于伪政,薄凉自私
。
而喜欢《诗经》里那古老的句子:“死生契阔,与子成说;执子之手,与子皆老”的张爱玲,真的这样去爱了胡兰成与赖雅,既有现代女子的浪漫自主,更有古代女子的深情专注,率性而爱,情比金坚。

从《今生今世》书中可以看出,胡对张是一种不当回事的态度,觉得张怎样都是对他倾心的那种人。
他甚至搬出张自己说的话“你就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,也是可以的”来证明,这是很不公道的态度,滥用人家的宽容。女人是不可以太受委屈的,可以和你同担风雨苦难是一回事,但是轻易散漫对待是另一回事。
而胡的却把风流情怀当成一件可以炫耀的事情,可是他遇到的偏偏是张这种人物。
他以为他是既可以明媒正娶,又可以金屋藏娇;既可以温玉满怀,又可以猩猩相惜,这样的如意算盘估计是许多男人都有的,但绝不是好男人的样子。
张爱玲的清坚和坚绝是对他人生态度的一记嘲讽。
如此,我还是敬佩张对胡的态度,从此相忘于江湖吧,过去就一笔钩销
。可怜张唯一一次的相爱,遇人不淑,惨痛至此,如她所说:“我将只是萎谢了”。
尽管如此,从《今生今世》看,张对胡仍是仁义至尽,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付出多余索取。从这方面来看,张的人生境界是高于胡的。
胡通篇都是我我我的
,张对他却是真爱,所以眼里却只有你你你
。爱就是爱,不问为什么,无论胡是个什么角色,能够让张“低到尘埃里,开出花来”的也只有胡兰成这个人了。可张还是“与君醉笑三千场,不诉离伤”。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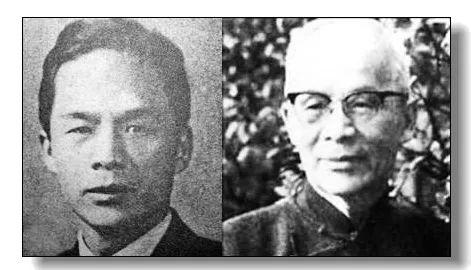
胡兰成当然也有文才,这是勿容置疑的,不然一个汪精卫手下的笔杆子,属于没有气节的无行才子一类,一个用情不专的无行文人,既没有民族气节又薄情寡义的人
,为何能降伏张爱玲这样眼高过顶的才女呢?香港评论家江弱水用九个字概括胡兰成:“其人可废,其文不可废。”
而正是这无法回避的文才,深深打动了张爱玲
。我看有不少论者都认为胡兰成的文章写得比张爱玲还好,这种说法恐怕胡兰成本人是最乐意听到的,因为他晚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写出一本比张爱玲的小说更优秀的书来。
但我不这么认为。
止庵先生为《今生今世》中文版作序时写道:
“我又曾提出有一路‘才子文章’,从林语堂、梁实秋、钱钟书直到董桥,皆属此列;现在不妨把胡兰成一并算上。才子者,首先真的有才;形之于文,是为才子文章。以此而论,胡兰成堪称就中翘楚,确实绝顶聪明,处处锋芒毕露。虽然,才本身有品,才之后有识有学。至少前一方面,作者不无亏欠;可是才气太大,似乎又能有所弥补。才子文章,无论意思文字,难免取巧做作,仿佛不甘寂寞,着意要引得读者叫好;胡文亦不例外。但是意思上能做作到‘透’,文字上能做作到‘拙’,这是其特别之处,自非一般肤浅流丽者可比。我读《今生今世》,觉得天花乱坠,却也戛戛独造;轻浮如云,而又深切入骨。”
这话语很是到位,也是江弱水那种意思:“
其人可废,其文不可废
。”作者:
山野樵夫:高校教师,喜文悦游。诗苗书叶,山水林田,也看风景也读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