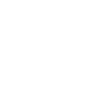编者的话
---------------
等下一个表白,等你
俱新超商洛学院学生
我是秦岭的孩子,是六亿年前出生的小娃。那时,我的周围是一片汪洋大海,海水不断变深,一股向上的力量隆起我形成了耀眼的褶皱。于是,我成了一个帅气、年轻的精神小伙,有人称我为山,有人喊我是崖,在众说纷纭中我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——太白山。长期以来,我银光四射,无数个世间人朝我涌来,向我诉说他们的故事,我想他们是在向我表白吧,表白珍藏于内心的喜怒哀乐。
寒冷对我来说最是欢喜,厚厚的雪覆盖在我身上,柔软、舒坦又保暖。极度寒冷的冬天,我昂起头颅,望着天,踩着地,载着向上攀爬的人们。那日,雪花洋洋洒洒地飘落在我的头上、身上。一位沧桑的老人,在众人的搀扶下一点一点费力地向上走着。我的眼眸里嘀嗒嘀嗒涌出了不尽的泪水,水滴顺着山谷缓缓向下流淌,一片树叶承载了我的泪,落在了这位老人的头上。
他弓着腰,拄着拐杖,气喘吁吁又筋疲力尽:“我的回忆山嘞,时隔五十年又来看你了。”我诧异,低头沉默,显然忘记了这位老人。泛红的太阳从山梁一侧升起,我的眼全然不能睁开,又生怕老人从我的视线里远去。他颤颤巍巍,却精力十足;挽起裤腿继续攀爬。我害羞,又想近距离看看这位老人的面容,再允许我思索一番五十年前的故事。
一路跌跌撞撞,周围的行人匆匆,都侧目注视着他,恍恍惚惚,他的身体透露着坚强,我听见一个高亢的声音:“老伴啊,我们就要登顶了。”拔仙台的最高处,我的肩膀上,站了一个倔强的老头,手里握着一张残破的照片,他抖了抖灰,吹了吹土,嘴里不停念着:“老伴啊,你还记得当年的冰雪吗?还记得我们一起穿过的古木栈道吗?还知道我们一起拜过的洞天福地吗?”
大雪纷飞中,我却清晰看见了他的模样,一如五十年前一样豪迈洒脱,如今他身着黑夜,面容苍老,却脚步沉稳。刹那间,我想起了五十年前的种种:夫妇两人互相搀扶着,一路抚携,相互鼓励,抵达山顶。下山的一刻,我听见他们约定着五十年后会再来一趟。如今,果真来了,我却不知所措,太白山啊,太白山,你有着多么亲密的挚友啊,他们是来向你深情表白的。一声声哭喊,一次次呼唤,大爷是痛苦的,他的老伴离开了人世,可依然要坚定地完成五十年前的承诺,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,迎着风,沐着雪,将自己身子缩了下去,洁白的雪埋葬了我。
“太白山,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了。老了,要和我老伴一起享福去了。”我目送着他走下山,看着他的背影,想起了若干年后的自己。他敲打着我,抚摸着我,深情告诉我:“守护城中老小,就靠你了。”是的,我接受他的表白,为的一切信我、爱我、亲我的世间人。
之后的许多年,络绎不绝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,有的是医生:“山啊,你何时才能抵挡住疾病?”有的是学生:“山啊,我何时才能学有所成?”有的是农民:“山啊,庄稼何时才能喜见丰收?”我气我不能说几句话给他们,我恨我动弹不得,让遥远的亲我者跋山涉水赶来向我告白。可是我想你们爬上山,再走下山,回家的途中转过身子看看我,天那么大,我是那般渺小,可我依然坚毅、顽强、不屈不挠,不畏严寒,站立在一方,你们真该如我一样精神抖擞地面对一切。
我的秦岭母亲高大巍峨。我悲,她便让我听听她的溪流,淙淙流淌,昼夜不息。于是,我便精神矍铄,巍然屹立。悲苦的世间人,如果有机会,我愿你亲近我、信任我、爱恋我,将你的疾苦说给我听,我会张开臂膀,欣然接受你的表白,再与你共担风雨。
等下一个表白,等你。
---------------
也许我等不到一个表白,也许我下一秒就等到
安妮郑州大学学生
我终于将心事付之于口,但结束一桩惴惴不安后旋即又陷入了另一桩焦灼。我此刻站立于春天夜晚的微风中,等候你的剖白。
诗人说,“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,梅花便落满了南山”。而我在等待的时刻,你的剖白却仿佛要跨越若干光年的距离,才能抵达我的耳中。
先是急煎煎的焦灼,我焦躁如三伏天太阳底下一只可怜的虫子,想要走开,但举目四望周围是同样的炙热,只能暗自忍耐。随后我陷落在惶惶的不安里,畏惧你不答复,畏惧你使我失望。
沉寂无声的四周空茫一片,只有我层层叠叠的想法茫然飘荡,盘旋升空。旁边湖中黯黯的水波漾着,偶有鱼尾巴扑一下水面,引起一点微澜,但很快就又消弭。就像我摇曳的想象在虚幻中凝出一点微弱的希望,很快又逸散了。一颗心只于渺茫中来去,没有着落,本应浮萍似的很轻盈,可是到底还有隐绰的一点,对你表白的期盼,藏在那样深的心底,却像一件沉重的枷锁坠在脖子上,坠在心里。这沉甸甸的介质积压在心底,且愈发地重达千钧,几乎要将这颗胸膛里勃勃跳动的心挤碎,我的心就像一个揉皱了的干枯花朵,起先的焦灼消失不见,余下灌铅似的重量。
惶惶然的头脑,昏沉沉的心跳,我的脉搏和你的一同蓬蓬跃动。我和你共存于此刻的大地,沉静的长夜一般的寂静。我想太阳什么时候才能跃出,带来炯炯的哪怕只有一线的光。
这种等待断不是徒然的牺牲,不能斤斤两两地去称量,可又确实平白耗去了大量的心力。等待本身沉重而结果轻盈,只是你轻飘飘的几句话,而我对你究竟要说什么难以笃定,我所畏惧的就是这样的落差。
眼前仿佛起了一层虚幻的、莹莹温润的雾。等待于我已经太久,也许只过了一分钟,却这样难捱,以至于想起我等待的开端,都有一种陈旧的模糊,你在沉吟,在构建语言阐明你的想法,而我只能等待。此时寂寂的每一刹那,真长,长得百转千回,长得心头流水的一点微漾已入了海,不见波澜。
只觉得心里伤惨,五内如沸,汗水快要涔涔,几乎酸楚得想要落泪。影绰的云涌动着,静寂堆在四周。我的等候和你的面庞、此刻的天光、摇曳的柔嫩枝条一起铺展成大片的潮水淌过去,漫散到未知的地界。
现在,我在等待中幻想的时候,竟有一种别致的快感。盯着对面墙皮上,路灯光把树枝复杂枯涩的线条摹出的影子,有苦苦的黑灰色沾了一墙,随即所有层层叠叠的想法变成通天塔延伸到天际,或者潜入到海底,有如实质。
我注视路旁一条干瘪被人遗弃的面包,想象出在幽深海底沉睡多年的潜艇遗骸,凝望一枝委顿的花联想到光年外一颗巨大恒星的爆炸,壮丽如诗。
我也幻想到具象的日常生活。某个人,也许是邻居,也许是街坊,在七时一刻慌张地从床上拔起来,繁忙着嘈杂着活泼泼交响着的锅碗瓢盆和桌椅板凳,路上碰到熟人时漫不经心的陈旧问候和望向今日的困顿眼神。我幻想每个精确到毫末的细节,以至于在原地不动,我便看见想象中无数相仿的琐碎明天踱步走来。
炯炯燃烧的思想爆裂出的每一束火花,把刹那延展成无尽,映照每个明亮或潜隐的瞬间。幻想丰盈壮硕,盘旋上升成为存在于意志中的巴别塔,膨胀成为海底的巨兽或者天边的密云。
而当我的目光又复归于你的沉静的脸时,我的想象又触摸到了过去的日子。想起从前的时光,像毛茸茸的花拂过手指时一般的感觉,心里微动。
那时候大家去跑操的场面是校园最漂亮的风景。整个学校的学生都出动,挨挨挤挤地往前走。那么多乌黑的后脑勺和蓝色校服,我也可以一眼认出你。教导处的老师吹哨催促,于是我们全都涌动起来,像潮水一样接替。那条路沿途种了很多很多树,不同的种类,到了夏天就长得一样翠绿欲滴,有长长的延展的枝条,枝丫间透出明亮的光斑,跃动在我们同样蓬勃的年轻的脸上。路边有一个湖,有一小片芦苇,里面有暂时停驻在我们学校的迁徙落单的大鸟,不知道是什么品种,但是羽毛很美丽,尾羽长长的,骄傲地在湖上停留睥睨的样子,好像是国王在巡视领地。
湖连着小河,河上架着小桥,跨过桥就是操场。
你在队伍最前面领跑,我的位置在第一排的边角,我们同在跑步。任何普遍而统一的相仿都使我喜悦异常。我看着你的背影,好像我永远都只是看着你的背影。看你高高挥舞着的旗帜,意气风发的后脑勺,白色的运动袜,垂下又鼓起的衣角。
我记得在教学楼长长的环形回廊里,有一面墙上镶嵌了整面的单向玻璃,我站在二楼的玻璃背后,手里握着永远背不完的政治课本,看来来往往拥挤的人潮,看熟识的不熟识的一张张面孔渐渐走近,消失在楼道,或者走远,拐角就不见。
看到你的背影,意气风发的模样,渐渐远去,再也不见。
而此刻,我只是在等待。
也许我等不到一个表白,也许我下一秒就等到。
---------------
我不会一个人去看海
王近松贵州工贸职业学院教师
天空一如既往地晴朗,窗外摇曳的玉兰,在春天蠢蠢欲动。我希望你一直在,并且在等待中,让我可以有一个机会去学习爱与被爱的能力。
这是认识你的第476天,从2020年的冬天到2022年的春天,再也不像2019年在昆明时那样,傍晚喜欢沿着小路去看芦苇,去看落日,在遇见你的这些日子,我不会一个人去看海。
22岁,我不敢去谈论一生,我只知道,没有哪一场云海不值得期待、没有醒不来的噩梦。我越来越害怕遇见美好的事物,我生怕一个人见证了美好,那种单向的快乐算不上真正的快乐。
在认识你427天的时候,我给你发消息,给你写了这样一句话:“谢谢宝贝,在我最不理智的时候,依旧把我留在你的通讯录中,不管以后是否还会有一些矛盾?但你在我生命中,都是最重要的人。”在这句话后面,还打了一个括号,告诉你:“不准反驳。”
我们常说日子漫长,漫长的,恰恰是那些不愉快的时光。
在这一年的时间,给你写了3万多字,不能说字字珠玑,但每一个字都代表了对你的爱,尽管3万多字不能代表400多个日夜,只是我们都知道,在我们说爱之前,我们已经知道要沿着脚下的路,一点一点向前走。
为了一个镜头,我经常站在一个地方等待,就像一棵树如果没有雾,就会显得单薄;山川如果没有云海,就会显得深沉。为什么要选择等待?等待常常让人觉得美好,以至于我现在不愿意一个人去看海,又或者说这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海,所以当我站在海边,海中的倒影只有一个,就会觉得孤单。
我想等待,也愿意等。我见过最孤独的,莫过于太阳和月亮,它们从没有机会并肩前行,但有时候我们也能看到日月同辉的景象,这样的景象并不容易看到。我享有的权利,就是等待。我愿意等到樱花盛开,等到芦苇长出新苗。其实等待也像一面镜子,在镜子中便能看到自己,你并非彼岸花,只能远观,当我们慢慢靠近,才发现这个世界,在爱与被爱中,等待和接受如同狭义的哲学。我也需要自我认同,认同自己、认同爱、认同等待。在我等待的同时,我知道我会有一个被爱的机会,我也有机会去学习被爱的能力。
等待,其实也意味着诸多的不确定性。在每一个看似短暂的过程中,实则波涛汹涌,这种汹涌来自内心,来自内在的生活。在这之前,我始终无法确定等待的意义,当我每天从睡梦中醒来,内心深处是你、聊天界面是你的时候,我会偷偷窃喜,在22岁时,我相信等待会有结果,我也相信我不会一个人去看海。
背包里每天带着相机、无人机,其实也是在等待某一个瞬间。我无法将生活中的美好搬进梦境,对于我们来说,时间已经开始在绘制明天的天气,我也在绘制被表白的时光。
张万森和林北星是人间烟火,而我只要你一句表白,当然这种的奢侈是多余的,把那些表白的话留给我吧,等待了许久,爱才会有更大的爆发力。
“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安静下来,并慢慢懂得等待的意义。你或许曾像诗人卞之琳一样,在困倦的冬日午后,等待友人带来雪意和五点钟;又或许像木心先生一样也在大雪纷飞的暗夜里,独自等待过什么人。”
而我们,你只需记住等待与时间无关。
---------------
去厦门
杨鸿涛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生
阿汤忽然感到一滴清凉的山泉落在心上,当他听到梦梦的歌声时。
他已经搬了一下午的水泥了,太阳热辣辣地烤着,把他的背烤成了黑色。有些累,他便靠在一块板子上,掏出手机,刷抖音。阿汤是个内向而老成的人,手机里唯一的娱乐软件是版本很旧的开心消消乐。工友们笑他是个土包子,把他的手机抢过去,给他安装了抖音:“这里面的姑娘个个水灵!”于是阿汤也渐渐变成了他们的一员,休息的时候,就刷抖音、看直播。当他刷到一个叫“梦梦”的音乐主播时,野性而优美的歌声让阿汤的心震颤了一下,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觉,他给梦梦点了关注。
今天梦梦居然正在直播,“欢迎阿汤!”梦梦天真热情地说。阿汤突然有些紧张,又有些开心,已经很多年没有人向他表达过热烈的欢迎或者感谢了。过了三十岁以后,他变得沉默,不再有不切实际的幻想,决心安心当一个施工员,攒两年钱,买房子。每天在工地和出租屋之间徘徊,他习惯了闷头干活儿,除了工友们的调侃,一天听不见几句话也说不出几句话。
工友们也被歌声吸引,一窝蜂地涌上来,结果看到梦梦并不漂亮,右脸有明显的疤痕,直播间只有冷冷清清七八个人,于是大家又无趣地散开。眼前的这个女人确实不漂亮,也不年轻了,阿汤却对她产生一见如故的亲切。她没有开美颜特效,黑眼圈挂在眼睛下,很憔悴。
“阿汤,你想听什么呢?我为你唱一首吧。”阿汤感到心头一震,不安夹杂着兴奋,他想了一下,在屏幕上缓缓打出“春风十里”四个字,那是他从中学听到大学的歌。梦梦唱起来了,为阿汤一个人唱的。那声音多美妙啊,飞翔的鸟,巧克力,奔向远方的火车,阿汤的脑子里满是浪漫的幻象。隔着屏幕,两双眼睛深情地对视着,梦梦的眼睛很温柔,像两只弯弯的月亮,流出清澈的水来,流到阿汤的心窝子里去。他忘了自己是在一片充满钢筋混凝土味道的工地上,他感到自己脸上的臭汗消失了,站在一片辽阔的草原上,闻到青草的香味,他就要飞起来了……
后来,阿汤每天都会点进梦梦的直播间,那双温柔的眼睛泛出的善意,常常成为他入梦前的蜜语。工地上的华子用流行段子调侃他:“你惨啦,坠入爱河啦!”阿汤只是笑笑,他自己也不清楚,这种奇异的感觉,就是爱吗?也许,能算暗恋吧,暗恋一个网络女主播,大概有点可笑吧!阿汤想。
梦梦比想象中更坦诚一些,她说她已经二十八岁了,在打工,顺便在抖音上唱唱歌,能赚一点钱。基于梦梦的诚恳,阿汤也诚实地告诉她:“我已经三十二岁啦,在工地上干活儿。”梦梦告诉他,干活儿要保护好自己的腰,她的弟弟也在工地上,前一阵子把腰闪了。他们聊天的频率越来越高,梦梦善解人意,也懂得感恩。
过了很久,阿汤才敢问出那个简单而复杂的问题:“你……你单身吗?”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,当梦梦讲到她的经历时,阿汤常常主动岔开话题,他害怕知道答案。梦梦嘿嘿一笑:“说出来不怕你笑话,其实我还是‘母胎’。”梦梦的坦诚再一次打动了阿汤,他也是“母胎”单身,因不懂女孩子,三十多年来都没谈过恋爱,但是他却常常在朋友那里虚构出两三个女朋友来,以此维护自己脆弱的自尊心。“其实我也是母胎。”阿汤发出这句话,感到很踏实。他自己也没想到,当自己步入三十岁之后,真实而可靠的、初恋般的悸动居然是通过社交网络实现的。
那天,阿汤依然像平时一样观看梦梦的直播,突然,他注意到了她身后那片若隐若现的海,无比遥远却又无比熟悉。“这……是在鼓浪屿吗?”“是呀,这里就是鼓浪屿。”梦梦还说,她是厦门人,就住在附近的。厦门,于阿汤而言,是一个多么熟悉而温暖的词,几乎代表他的整个青春。他现在很少跟别人提起,自己是大学生,大学是在厦门念的,那四年他读了很多书,对法律很感兴趣,还考了律师证,他想以后做个律师。那几年阿汤还很活泼、炙热,喜欢唱歌,参加了学校的音乐社团,每天有讲不完的话。阿汤喜欢厦门的海,特别是鼓浪屿的海,海能给他一种力量。他是怎么来到贵州,变成一个沉默寡言的工人的呢……他不知道,一切都说不清楚。不过他感到身体里有一种气息被激活了,他萌生出一个很久都不敢想的想法:去厦门。
“如果我要来厦门找你,你会不会觉得很可笑?”
“如果你只是说说,我会觉得很可笑。”
“我会来的。”
“你不怕我是骗子吗……”梦梦说。阿汤也想过这个问题,他害怕“梦梦”真的只是个缥缈的幻梦。可是第二天一早,阿汤还是向工头请了假,事实上,他不一定会回来了。下午,阿汤踏上了去厦门的旅程,他要奔向暗恋已久的梦梦,更在奔向新生的自己。
---------------
无声告白
刘欢欢西南大学文学院学生
我们都在等何言表白。
今天是毕业聚餐,此后一别,相见寥寥。当初刚入大学时,绿荫成片,青春肆意又喧闹,而今四年一闪而过,当真是歌词所言“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,转眼就各奔东西”。班长组了个局,希望趁毕业前好好聚聚。即使也这样,班上的同学也没有到全,有人因为实习没返校,有人因为疫情暂时居家。看着坐在一起的大家,却感到圆满好像越来越难。
何言喜欢顾娟然已经整整三年了,一直没有表白。身为室友,我们却很难鼓励他,因为大概很少会有女生喜欢一个少年谢顶的男生——何言的脑袋和四五十岁的地中海男人没有区别。大学时代与纯美恋爱,这么青春美好的词,想想也就知道何言表白的结果会是什么。我们能理解这种结果,但正是因为能理解,事情才更多一层灰色。何言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和顾娟然表白,他每次看着顾娟然从身边走过,就像一个同学一样打招呼。同学,这是他们仅有的关系。但是,即将毕业的时候,何言却突然对我们说:他想表白。
越想敲的门大概敲得越轻。何言拒绝了玫瑰花拒绝了情书,甚至拒绝了微信上的一句“我喜欢你”,他只想在毕业聚餐上和顾娟然多说几句话,然后告诉她:他舍不得毕业,舍不得她。何言说“她”的时候,语气是那么轻那么轻,我甚至以为他不打算说出口,或者要把“她”变成“她们”。寝室的兄弟们都很关心何言,说反正要毕业了,就大胆一把,玫瑰花送过去吧。何言只回答说“不好意思”。晚上大家都睡了,我和何言的床抵着,何言突然开口:“我也很想送一束玫瑰,炽热的、鲜红的、浪漫的玫瑰……可是,我怕她难堪。”
在这个世界上,似乎有一套逻辑处于不败之地。那就是当某个肤浅的缺点太过耀眼时,人们只会关注肤浅。比如一个看起来笨拙、秃顶的男生手捧玫瑰表白时,打眼的不是玫瑰而是秃顶。
顾娟然毫无疑问是个好姑娘,她优秀、漂亮,对每个人都满怀温柔。一向不喝酒的女生们也有一些端起了酒杯,但是顾娟然没喝。何言一直在男生桌喝酒,我们几个冲他使眼色,何言当作没看到,又端起一杯。大家觉得今天是等不到何言的表白了,谁也不想看到顾娟然尴尬的神色,抑或是他人诧异、嘲讽的目光。
离散场越来越近了。我们结好账,却发现何言坐到了顾娟然的旁边。顾娟然没有流露出不耐烦或是讨厌的神色。何言在絮絮叨叨地说一些伤感的话,这不像平时的他。顾娟然边听边安慰他。室友上去拉何言,何言没动,他的头发向下耷拉着。
我们只好坐在隔壁桌。
何言絮叨了一会儿,又沉默了半晌。我们以为他再开口会说出那句话,但他只是呆呆的,低着头颅,酒精好像不仅麻醉了他的神经,也麻醉了他的心。然后,何言做了一件我们都没想到的事:他缓缓地抬起手,摸了摸自己的头顶,说,我没有头发。
只有顾娟然坐在他的身边。顾娟然明显愣了愣,随即故作轻松地说,没事啦,这只是一个不足嘛,努力挣钱努力生活,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。
我想何言大概是真的醉了,因为他接下来说,可是,很丑啊。
一种带点茫然又有点伤心的小孩子一样的语气——一个油光锃亮、中间漏风的脑袋无异于给所有诗一般的青春情怀宣判了死刑。顾娟然无法回应。她没法轻飘飘地说不丑,也没办法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,所有的话语和安慰都显得如此苍白。
室友搀着何言,今晚的告白大约是和夜色一起沉入海洋了。
稀疏的星,稀疏的蝉鸣,快要到路口时,何言突然大声唱起来:
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
谁安慰爱哭的你
谁把你的长发盘起
谁给你写的信
……
几个喝醉的男生受到感召似的立刻也跟着大唱起来,女生们哈哈大笑,也有的一起唱。我看向顾娟然,她没有唱歌也没有笑。
我们都在等何言的告白,何言在等毕业聚餐这一天。也许那无声的告白,就在何言的歌声里,在三年不知不觉的时光中。
来源:中国青年报
来源:中国青年报